必须承认,有关复仇的问题总是让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美国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如果一个人复仇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他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戴蒙德对比了两个人的真实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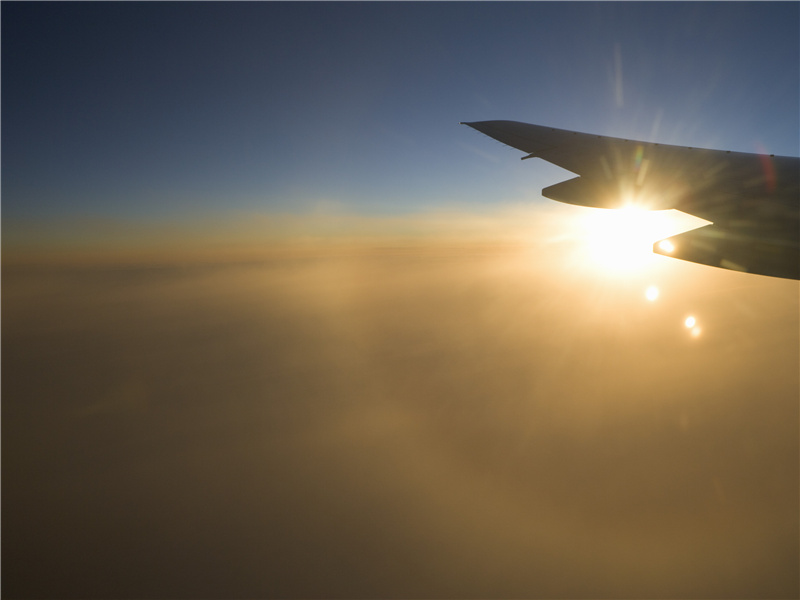
一个是他的朋友丹尼尔,这位新几内亚高地人成功地报了杀叔之仇;另一个是戴蒙德已经过世的岳父,他曾有机会杀死一个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残杀了他所有亲人的凶手,但他最终把这个人交给了警方。可是,凶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然后就重获自由。
在这两个故事中,一个人复仇成功,另一个人则放弃了复仇,这两种行为最终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虽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新几内亚高地的仇杀文化,但丹尼尔的复仇之举毕竟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而戴蒙德的岳父在此后的6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悔恨、内疚的折磨之中”。显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复仇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
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人视作自身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要求他承担责任,并认为这种罪行必须受到惩罚。而且通常来说,唯一合理的惩罚手段似乎就是让行凶者承受痛苦,或者剥夺他的生命。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一个以科学事实为审判依据的司法体制是否能够抑制这种复仇冲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够将人类行为背后的各种原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这至少在一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对不义行为的自然反应。
例如,如果戴蒙德岳父的家人是被一头大象践踏而死,或者死于霍乱感染,那么我相信戴蒙德岳父所承受的痛苦会有所不同。我们也同样相信,如果戴蒙德的岳父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杀害他家人的凶手原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而这个人之所以会犯下罪行,是因为大脑前额叶皮层受到某种病毒的侵害,那么他心中的悔恨也会缓解不少。
然而,复仇的“假象”仍然符合道德的原则,甚至是必不可少——如果它的确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对某些罪犯进行严惩(而非遏制或恢复)的做法是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复仇的欲望,是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自身思想、行为的绝对主宰,因此,复仇的欲望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认知与情感的错觉之上,并由此产生出一种道德的错觉。
在探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因为慑于事后的惩罚而中止实施时,我们才会将相应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身上。我们无权让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打喷嚏定为一种罪行,那么无论面临的惩罚有多么严重,总会有人违反这条法律。然而,对于绑架一类的行为,实施者需要一步步地精心谋划,付之行动,因此威慑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惩罚的威胁可以让你中止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行为就恰好印证了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
为了防止某些罪行的发生,严厉的惩罚也许真的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不能仅仅依靠遏制性或者恢复性的措施。但是,这种纯粹基于实用目的而采取的惩罚举措,与我们目前所实施的惩罚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对细菌与病毒的惩罚可以防止大规模传染疾病的发生,我们同样应该将它们绳之于法。
赏善罚恶的措施可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它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社会惯例。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格纳(Daniel Wegner)所指出的,自由意志观念可以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把钥匙。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在牌桌上挥霍掉一生的积蓄,我们会说他自作自受,这句话的含义是,他本来完全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他的一切行为都源于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沉湎赌博,并非由于偶然的因素,也并非是受到某种幻觉的控制,而是出于他自己一步步的意愿、想法和决定。
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可以忽略那些潜藏在各种欲望、意愿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说基因结构、突触电位,等等,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有关人类行为的传统认识之上。当我们思考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时,我们往往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合理建构自我思想、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我要的是啤酒而不是红酒?因为我喜欢啤酒。那为什么我喜欢啤酒呢?我无法解释,但我通常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我只要知道自己喜欢啤酒而非红酒就已经完全足够。无论原因是什么,反正相对于红酒来说,我更喜欢啤酒的口味。这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显然没有。如果我决定违背自己的偏好去选择红酒,这是否意味着我神奇地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反常的决定其实与你自身的偏好一样,都根源于无法解释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