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人类学中的文化地理学轨迹
虽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但是音乐里充满了地理空间概念和想象。音乐怎样给予我们地域感?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说法(1990,转引马钉斯托克斯,《族群性,认同与音乐:音乐的地域构筑》,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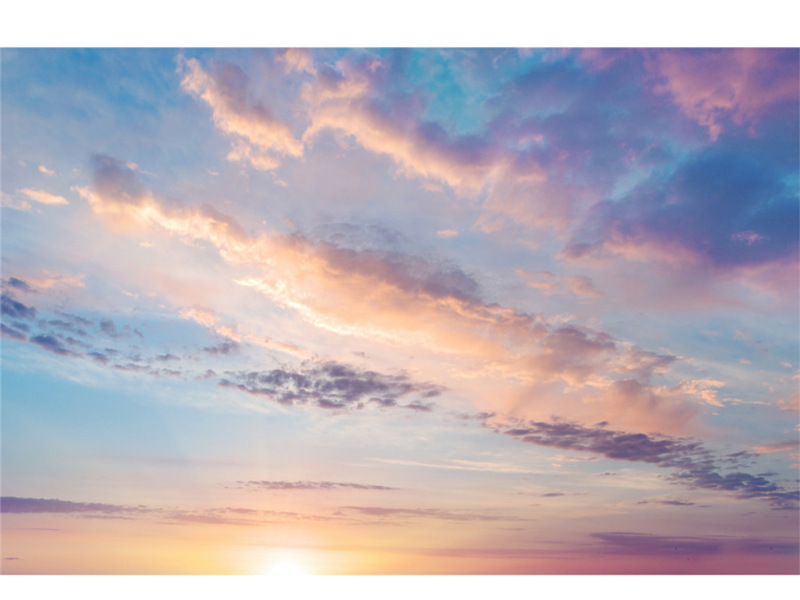
地域(place),或地点(locate)“指社会活动具体的地理背景”。他还指出,现代性一个明显的结果是“幻觉般地”将空间从地域中分离出来,因为地域已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力量所完全渗透,并按这种力量来塑造自己”(出处同上)。这一错位要求一种摆脱焦虑的重新定位过程,或者用吉登斯的措辞“重新植入”(reembedding)。在我们“重新定位”的无数种方法中,音乐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音乐事件——从集体舞蹈到播放卡带或CD唱片——唤起并组织集体记忆,展现地域的经历,其强度、力量和简单是任何其他社会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通过音乐构筑的“地域”,涉及差异和社会界限的概念。地域也构成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等级。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音乐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顾名思义,其“世界”的定语以地理范畴界定,正如《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2006版)所下最新定义:
(世界音乐是)结合来自非洲、东欧、亚洲、南美和中美、加勒比,以及非主流的西方民间音乐的多种风格的音乐体裁。最初杜撰该名称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英美发行的非英语的音像制品的激增的一个回应,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音乐已经成为真正的音乐体裁,成为西方流行音乐日益混合的音响的对应乐种。起初,非洲音乐就等同于世界音乐……至21世纪,世界音乐更加无所不包:既有巴基斯坦歌手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的歌唱,法国组合“吉普赛王”的流行弗拉明戈舞曲,也有用最新水准的节奏编程的融合少数族裔人声的“氛围–全球”(ambient-global)音乐。
世界音乐的上述定义开宗明义的关键词是“结合……多种风格的音乐体裁”,上述例子里隐含着不同层次的地理空间:一个国家的传统与现代空间(如巴基斯坦),一个大洲的空间(非洲),跨地区的空间(法国、吉普赛和西班牙),跨族群的想象空间(“氛围–全球”音乐)。
研究世界音乐的主要学科称作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亦译“民族音乐学”),该学科里也充满了文化地理学的范畴与概念。在评述手头这本《世界音乐》之前,有必要对其母学科的背景,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地理学的倾向,做一概要式的综述。对世界音乐的记录和描绘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家蒙田1580年的文章《论食人部落》(见其散文集),也许是现代欧洲第一篇关于世界音乐的民族志记载,评述了巴西(当时是法国殖民地)里约热内卢海湾一小岛上美洲土著的歌曲,材料来自加尔文派传教士让·德·莱里(参见第一章)1578年的记述。而最早杜撰“世界音乐”这一名称的是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巨著《世界音乐》(1650)。基歇尔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充满了科学好奇心和神秘性,其目的是汇聚一个音乐的世界。如同收集、展览古玩那样展示音乐珍奇,结合美洲土著及各国的音乐资料,展示各民族地区的仪式舞、乐器图像、音程表、记谱、音阶结构的数学图表,表现出以普同主义概括世界音乐的意图。
欧洲人研究世界音乐,其理论依据则源自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百科全书派的领袖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音乐辞典》(1768)反映了18世纪的这种时代精神。该辞典系统地使用了世界音乐的材料,目的是完整地概括音乐的定义。“为了让读者能够判断不同民族的不同音乐方言”,卢梭在论音乐的条目中展示了世界音乐的谱例,包括中国、波斯、加拿大的所谓“蛮族”歌曲以及瑞士放牧调。他由此得出音乐现象中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二元论,即文化普同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理性思想。
18世纪是启蒙运动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方地理探索的时代,崇尚实地考察的时代,因此“田野工作”兴盛起来,出现了许多基于第一手资料的著述,外交官、传教士、商人利用自己在中东、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的经历,撰写了许多关于东方音乐的第一手专著。启蒙运动对世界音乐研究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他者”(other)的概念,即非西方世界,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历史与文化。通过观察“他者”的音乐来影射、重新审视欧洲自己的音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学术界,这类对殖民地文化与社会的研究首先是地理学范畴的,之后又分化出一门新的学科——人类学,那是西方为了殖民地统治和治理而新建立的学科,以别于先前已有的研究西方自己社会的社会学。同时,在音乐方面还孕育了19世纪发展起来的东方主义音乐学(尤其是阿拉伯音乐文化)和比较音乐学。在19世纪,我们也看到了地理学、人类学、音乐学等多门学科的相交融合。
1885年,维也纳音乐学家阿德勒以比较的概念创立了一门新学科——比较音乐学,其核心也是从地理学不同层次的地域空间的范畴研究世界的音乐文化,即“比较音乐作品,尤其是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民歌,并按其不同特点分类、整理”。比较音乐学以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组织有关世界音乐的知识,时间方面吸取了地质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空间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即是地理学。1860年,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Adolf P.W. Bastian)首先提出“地理区”的概念,即在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的制约下,“原始观念”形成为具体的“民族观念”,此即“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思想影响了另一位德国人类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他创立了文化地理学,指出地理环境造成了各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此即文化传播理论的基础之一。20世纪初的一位德国人类学家格雷布纳(Robert Fritz Graebner)由此提出了“文化圈”、“文化层”以及“传播论”学说。他认为具有相似物质、精神文化的民族同属一个文化圈,圈与圈的相叠就构成了文化层;每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域一次产生并向四周传播的,这种传播的过程便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基本内容,这就是德奥文化史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一学派也援引音乐为例来证实文化传播的理论。如德国人类学家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考察了非洲的鼓,划分出四个文化区:黑人区,马来黑人区,印度黑人区以及闪族黑人区,各区都有自己的一类鼓。音乐学内则有萨克斯结合时空维度提出的世界乐器三大区理论,即初期层(旧石器时代,遍布全世界),中期层(新石器时代,仅分布于几大洲)以及近期层(新石器时代晚期,仅局限于几个地区)。
20世纪初,欧洲的比较音乐学家以文化普同主义的精神——进化论和文化圈理论,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雄心勃勃地试图绘制全世界的音乐风格、乐器和音体系的地图,与此同时,以博阿兹(Franz Boaz)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则切切实实地在自己“家里”做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用留声机录下即将消亡的一个又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音乐。他们引入了欧洲文化地理学、比较音乐学的“文化区”概念。博阿兹的弟子赫尔佐克和罗伯茨(Helen H. Roberts)借此概念,通过比较乐器,对整个北美大陆的印第安风格区进行了界定。
随着二战的结束,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了音乐人类学,最初的研究目标是,“所有非欧洲的音乐和乐器,包括所谓的原始民族和东方文明国家”(孔斯特[Jaap Kunst],《音乐学》,1950)。之后将近40年,音乐人类学内部由社会文化学派(以梅里亚姆[Alan Merriam]为代表)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学派先是以静态的文化共时主义关注封闭空间的地域性音乐文化,20世纪80年代起又倾向于时间的维度——音乐文化的变化,即动态的历时性;其间又出现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介入,与新历史主义同时出现了新文化地理学的空间理论。在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的《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为音乐人类学所下的最新定义里可以发现这样的空间范畴,即“在地域与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音乐的社会和文化方面”。这方面的典型著作如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的《声音景观:在变化的世界中探索音乐》(2006),运用了文化地理学的景观框架——空间背景中的声音及其意义——来探讨世界音乐,尤其是音乐的空间传播,涉及移民(时空变迁)、记忆(想象的空间),以及全球的市场(实际与想象的空间),凸显了当今世界音乐的空间流动性(fluidity)。其中音乐与移民的关系——时空变迁与音乐文化的互动——成为近十多年来的热点课题。“音乐不仅局限于单一地域,音乐的含义也不止一个地理来源”,音乐人类学“对静态的封闭的地域文化研究,转变成了对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里重要的文化地理学理论的研究学者还有图里诺(Thomas Turino),他结合了多重地域说(“同心圆背景”)与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音乐实践理论。他认为,政治、经济的历史与现实背景的变化首先改变了人们的“主观习性”(habitus,存在及认知方式),于是造成了音乐实践的变化。这里涉及国际–国家–地区这样三个层次的空间背景。音乐实践最高一层是国际的背景,即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及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帝国主义方针(经济、文化入侵);中层背景,即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西方这类入侵进行西方化的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再加上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助长了移民和城市化;在底层背景里,城市化吸引了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造成农村人口锐减,乐手流失。面临新的变化了的条件,人们有策略地灵活行事,对音乐实践做出相应变化,既维持又变化了传统。
另一更为重要的空间理论体系,可见于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斯洛宾(Mark Slobin)在《西方的微观音乐:比较研究法》(“Micromusics of the West: A Comparative Approach”,Ethnomusicology,1/1993)提出的世界音乐的文化空间的三种视角:(1)借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全球文化经济”的“景观”(-scape)体系(2)“可见性”(visibility)(3)文化三分法:亚文化(subculture),主文化(superculture),和跨文化(interculture)。
空间流动性景观(landscape),即人口景观、技术景观、经济景观、传媒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人口景观叙述“旅游者、移民、难民、流亡者、外籍工人及其他流动群体和个人”,已不再仅仅叙述民族志作者用作标准单位的比较传统的稳定人口,因为流动群体比以往更突出可见,更有影响;即使在国内,人口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异化也“打破了地域界限”。技术景观的特征是“技术超常的传播”。金钱的离奇运作则产生了不稳定的经济景观。意义深刻的传媒景观“往往围绕形象,以叙述说明事实”。意识形态景观即各种概念领域,源于欧美启蒙运动,现流行于全世界。以这套世界景观看音乐,音乐在技术与传媒的运动中漂泊不定,并为音乐创造者不断地打破地域界限而困惑。音乐被编入文化织体之中,由日益发展的技术所创造,由媒介传播,通过市场销售,表现出人们自律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人口迁移的控制。
世界音乐是一系列流动的风格、曲目与实践,地域上能伸能缩,不再是一系列历史地理渊源单一的有界实体,因而斯洛宾提出了有关全球音乐的另一种不同的关系体系,即“可见性”——观众的“可知性”——的分析角度。该体系分为地域、区域、跨区域这样三个层次。地域音乐是一定的小范围观众所知的音乐。这一类音乐是所有音乐人类学传统上研究的,即“族群”(ethnic group)的音乐,但这类音乐正日益减少,可是它们是音乐宝库的地域性话语,是身份认同的标志。区域音乐不易界定,若“地域”指一个村子,那么“区域”就再大些,如斯堪的纳维亚也可算一种区域,因为该地区几个国家都有一种波尔什卡(polksa)的舞曲形式。区域音乐也出现在与“流散地”——远离祖国却有类似音乐的群体——的联系之中。如美国的波兰波尔卡区域即是由一个个相距很远的城市连接而成。跨区域音乐能量很大,也许会成为全球音乐。
最后是音乐文化的三分法:主文化,即主导文化,可再分为工业主文化和国家主文化;亚文化是指弱势群体的非主流文化(如下层阶级,少数族裔,女性);跨文化再可分为工业跨文化和流散地跨文化。这里既有实际空间,也有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