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总督威廉姆·布拉福德 (William Bradford)、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主席布里格姆·杨 (Brigham Young)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朋友杰拉德·奥尼尔(Gerard O'Neill)有许多共同之处。三者都有远见卓识。他们都热忱地相信普通男女有走进荒野并创建一个比他们抛诸身后的社会更好的社会的能力。他们都为后人写了一来记录他们的远见和奋斗。他们都牢牢扎根在政治财务世界的真实土壤中。他们都敏锐地知道,要使他们的梦想变为现实,英镑或者美元有多重要。
布拉福德和杨的历史在他们生前并没有付印,而是以手稿的形式成为其追随者的指南。布拉福德的手稿在两个世纪以后以“普利茅斯开拓史”(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的题目出版。在摩门教堂的正式历史里,杨的手稿广被征引--虽然不是完全的。幸运的是,奥尼尔的书,《高边疆》(The High Frontier ),不用等到作者身后才能出版了。
将来的太空殖民者需要面对的人类和经济问题,和1620年的布拉福德及1847年的杨所面对的问题并无什么本质性的不同。不幸的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奢侈方式和过度花费,给公众的头脑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人类的太空活动必定要花费数以百亿计的美元。我相信这种印象基本上是错的。如果我们拒绝阿波罗的方式而采用“五月花号”(Mayflower)和摩门教徒的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太空移民的花费可以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我所谓“一个合理的水平”指的是可以和清教徒 及摩门教徒们筹集的总钱数相当的钱数。
关于筹措资金方面所遭遇的困难,布拉福德和杨提供了充分的史料证据。布拉福德在他的书里强调,在整个殖民冒险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确定一系列同胞们都能同意的目标:
但是正如在所有的事务中一样,涉及行动的部分最为困难,尤其是在那种许多代理人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工作上--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一些本该去的人打了退堂鼓,不愿意去了,留在了英国;一些商人和朋友已经提出为探险投钱,但是却退缩了,还找了种种借口;一些人非圭亚那(Guiana)不去;另外一些人则觉得除非是弗吉尼亚(Virginia),否则不会投资一分钱。而我们最仰仗的一些人却极度讨厌弗吉尼亚,如果他们去那里,这些人什么也不会做。
没有目标上的一致,筹钱的任务就变得不可能了。这种生活的事实,在今天就如同在1620年一样真实。在他们的历史中,布拉福德和杨描述了在目标和财务上的基本争端,其篇幅比他们对旅程的描述还多。当犹豫不决带来的痛苦结束的时候,两个人都庆幸地舒了口气,他们最终能够把注意力从政治和财务问题转向更简单的生存问题了。下面是杨在1847年2月冬季里写下的,那是在他横跨平原之前六周: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在冬日的风暴中被一群孩子包围着的父亲,我在以冷静、信心和耐性期待着拨云见日,那样我就能跑出去播种耕耘,就能收获玉米和小麦,我就能说,孩子们,回家吧,冬季又要来了,这里有家,有木柴、面粉、饭菜、肉、马铃薯、西葫芦、洋葱、卷心菜,所有的东西都管够,我已经准备好要屠宰肥硕的小牛,我要给所有归来的人准备欢快的宴会。我做了我在此处能做的一切,我满足于最后什么都会圆圆满满。
但是我必须从这些田园诗般的感受回到纯经济问题上来。两年前,杨报告说:
每一个五口之家所需要的装备有:一辆不错的四轮马车、三个牛轭、两头奶牛、两头肉牛、三只羊、一千磅面粉、二十磅糖、一把来复枪和若干火药、一顶帐篷和帐篷柱子--如果一家人除了寝具和炊具之外别无所有,要让他们能够启程出发,得有大概250美元的费用,而包括家人在内的整个载重量大概是2700(磅)。
艺术也在杨的预算之内。1845年11月1日,他花了150美元为吹奏乐队添置了乐器。这是个明智的投资,因为:
乐队有时会被邀请到行进中的队伍边上的村落里举行音乐会,这对于消弭这些地方偶尔持有的敌意极有帮助。所以,这支乐队除了能够鼓舞朝圣者的士气之外,对于行进中的队伍实在有绝大的好处。
事实上和杨一同横跨平原的,有1891个人、623辆马车、131匹马、44头骡子、2012头公牛、983头奶牛、334头散养的牛、654只羊、237头猪、904只鸡。
所以我们可以估计杨的远征队伍的总负载是3500吨,主要是一些活的动物,而其总价值是1847年的150000美元。
可惜布拉福德没有为“五月花号”提供这样一份精确的账单。他援引过罗伯特·库斯曼(Robert Cushman)的一封信,这封信是1620年6月10日在伦敦写的,那是起航前两个月。库斯曼是负责向航行提供粮食的人之一。
亲爱的朋友,我收到你的好几封信了,充满感情、抱怨,还有些我不知道的你对我的看法。对于你嚷嚷“渎职,渎职,渎职”,我惊奇的是一个如此渎职的人为什么能被用在这样的事情上。……靠150个人的财力,不可能筹到你所预想的多于1200英镑的钱,况且一些衣服鞋袜尚未计算在内--所以我们至少还缺300或者400英镑。我原来会削减啤酒和其他供给,因为还希望有其他冒险;现在,在阿姆斯特丹和肯特,我们都有了足够的啤酒可用,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毫无偏见地接受它……你说500英镑就够了;至于在这里以及荷兰的其余用度之需,我们再设法张罗。……事情要往好处想,对于我们需要的,我们该有耐性,上帝会指引我们的。
你亲爱的朋友,罗伯特·库斯曼
这封信显示,库斯曼个人承担的费用达到1500英镑。它并没有说是否所有的费用--特别是租用“五月花号”的费用,都包含在这个数字中。
三周之后,即1620年7月1日,种植者和冒险家之间签订了一个协议。种植者是殖民者。而冒险家是股东,他们往这项事业里面投钱,但是待在自己家里。协议规定“七年之末,资本及收益,也即房屋、土地、货物,以及动产,在冒险家和种植者之间平分”。协议的另一个条款是给每一个种植者一股,作为他们七年辛勤劳作的红利:“届时年满16岁或者年龄更大的人都会被估价10英镑,而10英镑即为一股。”种植者贡献出来的任何现金都会使他们获得额外的股份。
1620年的协议最终被证明是令双方都不满意的,它引起了经常性的冲突。1626年,也就是计划中分割财产的前一年,双方之间重新进行谈判并签署了一份新协议--“由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法律顾问起草,为的是使它牢固”。1626年协议规定冒险家向种植者出售“总价1800英镑(以下述途径或形式支付)的……全部债券、股份、土地、商品、动产……及任何增值部分或属于前述冒险家群体的财产”。 买下冒险家的股份后,种植园主们负债1800英镑--22年后他们成功地偿还了。
我不知道在1626年的处置中冒险家到底获益或损失多少。我也不知道远征的最初费用里种植者们到底承担了多大份额。就第一点看,冒险家不太可能亏损了,因为在1626年殖民地并不是没有偿还能力,而冒险家也不会白白借钱给人。至于第二点,种植者支付的费用似乎没有超过原费用的一半。如果他们支付了一半,他们可能就已经勒紧裤腰带把费用降下来了。那样的话,没有冒险家他们就可以干了,也大可不必让合伙关系带来的不可胜数的麻烦把自己弄得头疼不已了。所以,我从1626年的处置推断,对于租用“五月花号”及储备所需的物资,3600镑已经是初始费用的上限了。库斯曼信件这一证据暗示,这个费用的下限是1500镑。我用1620年的2500镑来估计这次远征的费用。无论如何,这数字不会误差两倍之多。关于“五月花号”的负载,布拉福德是明确说过的--180吨。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把1620年和1847年的费用数据转换成现代值。关于英国的工资及物价史,一个好的信息来源是恩斯特·菲尔普斯·布朗(Ernest Phelps Brown )及塞拉·霍普金斯(Sheila Hopkins)的工作。这一工作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经济学人》(Economica )杂志上,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一个叫作“经济史论文集”的系列文集里面重印了这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处理工资,第二篇则处理物价。到底倾向于以工资还是以物价作为基础去比较不同世纪的费用,那是个偏好的问题。如果使用工资,我们就是在说1620年一个劳动者的一小时相当于1979年的一小时。如果使用物价,我们就是在说1620年的一磅黄油相当于今天的一磅黄油。我个人的观点是,作为比较的标准,工资比物价更真实。我做这样一种比较的目的,是想以一种定量的方式去度量“五月花号”和摩门教徒的远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
根据菲尔普斯·布朗及霍普金斯的研究,在1620年,一个建筑业工人的日工资是8~12便士。在1847年,这个范围是33~49便士。关于这些数字在现代的相当值,我取1975年建筑业工会协议规定的最低值,即每小时9.63美元。基于工资的交换率如下:
1620年的1英镑相当于1975年的2500美元;
1847年的1美元相当于1975年的100美元。
这些都是非常接近的数字。对于1620年数字的印证,可由前已提及的下述事实提供:愿意前往普利茅斯并为共同体免费工作七年的种植园主,都可以得到10英镑的工资。
以1975年的价值估算的总费用,“五月花号”是600万美元,摩门教徒的则是1500万美元。在此基础上,我写下了表1的头两列。对于这些数字,我想强调的是,“五月花号”和摩门教徒的远征都是很昂贵的事业。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他们每一个都达到了一群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的极限。
表1 4种远征的比较
(费用的兑换率基于建筑业工资)
(M代表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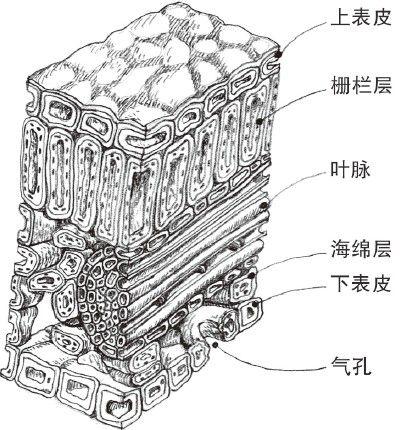
表1最后一行中的数字,是我估计的一个挣取平均工资的人储蓄其全部工资以支付其家庭殖民开支所需要的年数。虽然一个普通摩门教徒家庭的规模是“五月花号”上一个普通家庭规模的两倍,但以每户人工年计算的花费,“五月花号”上的种植者是摩门教徒们的三倍。这种差别对移民的财务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普通人,一心一意投身于一项事业,在朋友的少许帮助之下,能够储蓄其年收入的两到三倍之多。一个有一家人要养的普通人,无论如何投入,都不可能储蓄其收入的七倍。所以摩门教徒可以不负债,而“五月花号”上的种植园主却得被迫向投资者借入需要22年才能偿清的债务。每户两到七个人工年之间的某个数值,会是极限点,超出这个点,普通人以自助的方式筹钱就变得不可能了。
关于我的表中的最后两列,我什么都还没有说。它们代表太空殖民的两种可资对比的模式。它们都来自奥尼尔的书,我做了一些改动。第三列来自奥尼尔书的第8章,题目是“第一个新世界”,该章描述的是美国政府以正式的NASA方式开展的太空殖民。第四列来自奥尼尔书的第11章,题目是“小行星家园”,该章描述的是由一伙热心的爱好者们开展的“五月花号”式的太空殖民。
岛屿一号项目的开销是960亿美元。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对任何单独的事业来说,960亿美元都是近乎荒唐的天文数字。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数字。这数字是由一群有能力的工程师和会计们得到的,他们熟悉政府和航空航天工业的运作方式。它可能是我在表1中估计的开销中最精确的。用这960亿美元,你可以买一大堆硬件设施。在L5这个奇妙的殖民地--它距地球和月球的远近和这两个天体之间的远近一样--你可以买下整座浮动城市并用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安置1万居民。你可以购买足够多的人造农场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它会给殖民者提供食物、水和空气。你可以买下一个太空工厂,在那里殖民者可以建造太阳能发电站,将大量以微波形式存在的能量传递给地球上的接收器。所有这些有朝一日都会实现。正如奥尼尔宣称的--可能是真实的--经由出售电力带来收益,960亿美元的投资在24年内就能收回。如果债务能够在24年内偿清,那就差不多和“五月花号”的种植园主们能做到一样快了。但在岛屿一号和“五月花号”之间,有一种差别是无可避免的。表1的底部一行显示,如果岛屿一号殖民者要偿付整个费用中其家庭所要负担的份额,他需要工作1500年。这意味着,再怎么想象,岛屿一号都不可能被视为一种私人投资。它无可避免要成为政府项目,具有官僚化的管理,在危急关头必定是以国家为重,它必定要强制规定严格的健康和安全条例。一旦政府接手负责这样的项目,任何失败或者损失生命的严重风险,在政治上就都变得不可接受了。岛屿一号的花费变得昂贵的原因,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之昂贵在道理上是一样的。政府能够负担得起烧钱,但是它不能承担一场灾难的责任。
简单拜访完岛屿一号这个超级健康福利国,让我们继续看表1的最后一列。最后一列描述了奥尼尔的想象:一群青年拓荒者们存了足够的钱,他们依靠自己从L5殖民地搬出并进入小行星带的荒野之中。他们要冒单程旅行的风险。这里估计的费用只是期望而非事实。23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能够用100万美元装备这样一次远征,在今天还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可行。任何在专业上胜任这种估价的人,都会说这数字低得近乎荒唐。我倒不相信这数字低得荒唐。移民小行星的人均开支和“五月花号”的类似,这一点绝非偶然。地外空间将回馈给我们的,是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再拥有的开放前沿,而作为代价,这个数字已经是最高水平了。
按照表1的第三、四列,移民小行星的每磅费用并不比岛屿一号实质性地少太多。两种远征的巨大差别在于移民的数量和每人所携带的重量。小行星殖民这种廉价的空间殖民方式的可行性依赖于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家庭,人均携带两吨的重量,能到达小行星并建造一个家和一间温室吗,他们能在他们发现的土壤里播下种子和培育庄稼吗,他们能存活下来吗?这些就是“五月花号”和摩门教的移民们做的事情,如果太空移民们真的是自由而独立的,这些也是他们要做的。
还没有空间探测器访问过任何小行星。甚至都还没有科学仪器从小行星旁掠过以使我们对它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我们对于小行星们的地形和化学还很无知,正如在水手(Mariner)和海盗(Viking)计划之前,我们对火星也很无知。在不载人仪器探访过某些小行星之前,去预见殖民者在那里拓建家园时会面对的问题的细节,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了解小行星上的土壤是否足够松软而无需动用炸药去开垦之前,估计在小行星上开展农业的费用也并无意义。我不再去推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进行外太空殖民的动力机制的问题,我只提一些制度层面的理由来说明,想象从岛屿一号的960亿美元下降10万倍到达小行星家园的100万美元并非荒唐。首先,将人数从一万降至23,可以节省400倍。这样还剩250倍要削减。我们可望从自行承担一些风险和困难--政府是不会把这些加给它的雇员的--来节省10倍,另外5倍可以通过取消工会规则和官僚化管理来得到。最后5倍可能更难找点。它可能来自新技术,或者更加可能的,来自打捞和重新使用早期政府项目所留下来的设备。今天,除了月球上的,在环地轨道上,也有数百个被废弃的航天器等待我们的小行星殖民先驱们去收集和重新利用。
岛屿一号和小行星家园项目是极端的例子。我选择它们,只是为了说明殖民费用的上限和下限。真实的开销--一旦开始殖民--可能介乎两者之间。在这样困难和长远的投资中,还有进行混合模式的余地。在我们能弄清楚如何安全而廉价地殖民以前,政府层面、产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运作应该齐头并进,互相学习,彼此借鉴。只要能够得到,私人投资者需要一切来自政府和商业经验的帮助。在这种联系中,值得记取的是,哥伦布和“五月花号”的航行之间,横亘着128年的时间。在那128年间,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国王、女王或王子们在建造船只和建设商业基础设施,而正是这些才使得“五月花号”的远航能够付诸实施。
我和奥尼尔有一个梦:有朝一日,在太阳系及其以外,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小团体,会在空间自由扩展。也许这只是痴心妄想。正如布拉福德和杨了然于胸的,这是个很烧钱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去试,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