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休谟之外,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伟大的人物。他的父亲是柯卡尔迪城税务署的稽核,在亚当降生数月(1723年)去世。这位经济学家一生中几乎仅有的一次冒险,就是在他3岁那年,有一群流浪汉把他绑架,由于有人在后面追赶,他们把他弃置路旁。在克卡尔地求学一段时期,并在格拉斯哥上过哈奇森的几堂课之后,他南下前往牛津(1740年),他发现该校的教授真像后来吉本1752年描写的一般懒散、无能。亚当·斯密借阅读来自修,但学校当局没收了他手上那本休谟所著的《人性论》,理由是不适宜基督徒青年阅读。他认为和这些导师相处一年已足够。他很敬爱母亲,所以他回到克卡尔地,继续埋首于书堆中。1748年,他迁往爱丁堡,独立讲授文学与修辞学的课程。他的讨论给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1751年),其后一年又成为道德哲学的教授——这门学科包括伦理学、法律哲学、政治经济等学科。1759年,他印行了他的伦理学心得《论道德情操》(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巴克尔把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撇在一边,说这是“有史以来对这个有趣的题目所写的诸多著述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亚当·斯密演绎的伦理判断,其依据是假想我们置身于别人的地位时产生的自发的意向。我们因而和别人的感情产生共鸣,而由于这种共鸣我们才受到感动,开始赞同或谴责。道德感深植于我们的社会本能中,也就是深植于由于我们身为某团体的一分子而发展出来的精神习性。但这种道德感与自爱并不相悖。一个人道德发展的顶点是他以评判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时刻,“依据公正、自然律、谨慎和正义的客观原则来指导自己”。宗教不是我们道德感触的来源或主要依归,却因对一个主掌赏罚的上帝衍生的道德律的信仰而深受影响。
1764年,亚当·斯密41岁,应聘陪同18岁的巴克卢公爵环游欧洲,担任其私人教师兼向导。其薪资——终身300英镑的年薪——使斯密有撰述他那本杰作的安全感与闲暇。该书是他在图卢兹停留18个月期间着手著述的。他在费内拜访了伏尔泰,在巴黎会见了爱尔维修和达朗贝尔、凯奈和杜尔哥。1766年回苏格兰后,他前后和他母亲在克卡尔地很满足地住了10年之久,同时撰写他那。《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并接到休谟一封赞美函。其后不久休谟即告去世。
休谟自己在短论中屡次协助亚当·斯密以形成其经济与伦理观。他早已讥讽赞成保护关税及贸易专卖的“重商主义”、政府其他确保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的措施,及累积珍贵的金属以作为国家基本财富的办法。休谟说,这种政策如卖力地阻止水流向其自然水平流动一般。他呼吁经济应摆脱“欧洲各国,尤其是英格兰加在贸易方面的无数限制……与关税”而获得自由。斯密当然很熟悉凯奈及法国其他重农主义者反对同业公会和政府机构强行加诸工商业的规定的运动,还有他们要求顺其自然、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制定价格与工资的放任政策的主张。当时美国掀起对英国加于殖民地贸易限制的反抗,也是斯密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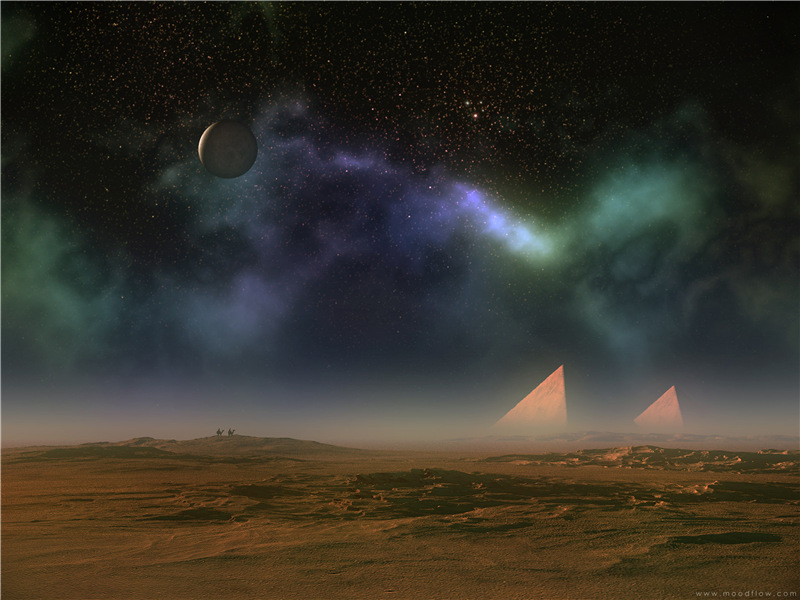
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和,斯密有一些看法。他认为英国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是一种“重商主义最卑鄙、最恶劣的权宜之计”。他建议:“如果殖民地的人民拒绝缴纳税捐来支持大英帝国的支出,那么不必经进一步争吵就应该让美国独立。”“以这种方式来和老友分手的话,殖民地居民对祖国天生的情分……自然很快重燃。可能使他们自然……在战争中或贸易中站在我们这一边,不但不会是狂乱、好结党的子民,反而会成为我们最忠实……最慷慨的友邦。”他又补充说:“由于该国在财富、人口及进展方面都有如此迅速的进步,不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也许美国的产物就会超过英国所课的税收。帝国的地位到时自然转移到帝国中为整体的防御与支持出力最多的那部分。”
斯密对国家的财富所下的定义,并不是该国拥有的金或银的数量,而是土地、土地改良及其产品,加上该国人民及其劳力、服务、技术与货物等。他的理论是,除了少数例外不计,最大的物质财富是源自最大的经济自由。自我利益虽然普遍,但是我们若让这一有力的动机随着最大的经济自由来运营,则必然促成工业、企业及竞争,其衍生的财富必然大于历史上任何已知的体系。(这正是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中完整地实现的。)斯密相信:市场的定律——尤其是供求法则——必可调和生产者的自由与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如若生产者获利过巨,则必有他人从事该行业,而相互的竞争必使价格与利润降至公平的限度内。犹有甚者,消费者能享受一种经济民主,借着购买或拒绝购买的方式,他大可决定应该生产何种货品,应该提供何种服务,及其数量和价格,这些事务都可不必由政府来指定。
亚当·斯密也赞成重农主义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劳动的产品和贸易的服务与土地的生产品一样,也是财富),他呼吁终止封建税制、同业公会约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规定及工商垄断,因为这些东西限制了某种自由——借着允许个人随心所欲地工作、用钱、储蓄、购买或贩卖的方式——这种自由可使生产与分配的巨轮转动不已。政府应采取放任政策,顺其自然——这是人类自然的习性。政府应容许个人自己改变职业,以尝试找寻自己胜任得了的工作、担当得了的职位。在经济生活中必须听任个人奋斗:
依据这种自然自由的制度,当权者(或国家)只须履行三种义务:第一,保护整个社会,使其不遭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与入侵;第二,尽一切方法来保护本社会中每一成员,使其不遭受其他成员的不平等对待或迫害,即建立确实执行正义的机构;第三,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及公共机构,此等工程或机构绝对不准许因任何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利益而兴建或维护。
这正是杰斐逊政府的方案,也是一个使新资本主义极度发展、极度繁荣的国家的蓝图。
不过,这个蓝图也有其美中不足的漏洞。假如防止不公平的责任即意味着避免智者、强者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愚者、弱者时,又将如何?斯密这样回答:“这种不公平只有在限制竞争或贸易的垄断情形下才会发生,而我的理论主张的正是解除此等垄断。我们必须让雇主争取工人及工人争取职位的这两种竞争来制定工资,政府规定这些价格的企图终必为市场的规律瓦解。虽然劳动(不是重农主义者主张的‘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是劳力是一种商品,正如资金一般,也受供需律的约束。”“尽管法令企图规定工人的工资,但总是想压低它,而不是想提高它。”因为,“只要立法机构想规定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差异时,其咨询的对象总是雇主”。这种论调写成文字时,英国法律允许雇主自己组织起来,以保障其经济利益,却不许受雇者这么做。亚当·斯密指责法律的这种偏袒,他还预见一个事实,那就是由政府的立法得不到较高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只有由劳动阶级组织起来才能获得。
这位资本主义先锋,几乎总是站在工人这一边,反对雇主。他更警告过,不可以让商人和制造业者来决定政府的政策:
商人的利益……不管是任何一种贸易或制造业,在某些方面说来总是跟大众的利益相异,有时更是相冲突……由这种次序产生的任何一种有关立新法的建议或对商业规定的建议都得谨慎地去考察……提出这些建议的那一帮人……通常总是喜欢欺骗大众,甚至还迫害大众,而且这些人……曾经好几次确实欺骗又压迫过大众。
这到底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的论调呢?不过,斯密认为私有财产是企业不可或缺的激素,因而大力为之辩护。他同时还主张:“工作机会和支付薪水的多寡,主要还是取决于资本的累积和应用。”不过,他声称高薪资对雇主、受雇人双方皆有利,他还劝人废弃奴隶制度,所持理由是:“归根结底算起来,自由民所做工作的工资远比奴隶所做的还要便宜许多。”
我们想到斯密本人——他的容貌、习惯和个性时——我们不禁怀疑:一个如此与农业、工业和商业秩序隔离的人,对如此奥秘、复杂的事物居然能写得这么实际,有这种洞察力与胆识。他和约翰·牛顿一样心不在焉,对习俗也很不在乎。通常,他很有礼貌、性情温和,而且能以4个字的反驳来迎击约翰逊的粗野举动,使人对“文坛权威”(指约翰逊)地位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在出版那本《国富论》之后,他在伦敦待了两年,认识了吉本、雷诺兹、伯克等人。1778年,他——这位自由贸易的使徒——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兼盐税司司长。嗣后,他在爱丁堡和母亲度其余年,至死未婚。他母亲死于1784年。他也在1790年随她去世,享年67岁。
他的成就与其说在于他思想的独创,倒不如说在于他对资料的熟悉和组合。那一大堆列举出来的材料启发性极浓地将理论用于当时的情况下,文体简洁、有说服力及他宽阔的视界,使经济学从“黯淡的科学”提升为哲学的水平。他这之所以划时代,是因为它综合了、解释了——当然并没有制造——那些将封建主义与重商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的事实与力量。小皮特将茶税的税率从119%降低为12.5%,还尝试着普遍实施较自由的贸易时,他对《国富论》的启示怀着受惠感激之情。罗斯伯里爵士还提到过在某次皮特也参加的宴席上,斯密走进来时全体起立,皮特还说:“你不坐下我们就一直站着,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弟子。”普尔特尼爵士也预言说亚当·斯密的巨著“必定能说服我们这一代,支配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