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巴黎市民的生活与喜好来说,剧院超过了沙龙。伏尔泰于1745年向马蒙泰尔说道:“剧院是最迷人的,它可以使你在一天中名利双收。一出成功的演出即能使一个人同时致富而名闻朝野。”各省都有好的剧院,许多富人家里另有私人剧场,在国王面前与凡尔赛宫廷,也演出戏剧,但只有在巴黎,人们对戏剧的热衷变成一股争论与快乐的热潮。剧作与演出的最高标准,都由法兰西剧院中的法兰西喜剧维持着;但更多的观众涌向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
所有这些剧院及在皇家宫殿的歌剧院,都是很宽阔的椭圆形大厅,里面有好几排座位,专为那些最高贵的观众而设;较次要的观众,就地站着观赏,而这种站着观赏的地方,我们误称为剧场(orchestra)。实际上,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剧院里是不设置座位的。约有150位纨绔公子或热心观众,因付了特别费而坐在剧台上,分三侧环绕着表演。伏尔泰曾经指责这种恶习妨碍了台上的演员和布景。他说:“因此,我们大多数的表演,除了长长的演讲外别无他物,所有剧中的动作都无法施展,或虽然演出,也显得那样的可笑。”他又问道,在这样的舞台上与这样的布景下,一个演员如何能扮演出在恺撒被刺杀后,布鲁图斯及随后安东尼对罗马民众的慷慨演说?而《哈姆雷特》剧中那个可怜鬼魂,又如何看得出那些享有特权者的端底?在这样的条件下,莎士比亚的戏剧几乎没有任何一出能在舞台上演出。伏尔泰的激烈抗驳,得到了狄德罗与其他人士的附和,最后终于收到效果。1759年,法国各剧院的舞台都已清理一空。
然而,伏尔泰在他为改进演员宗教地位的奋斗中,却不如此成功。在社会方面,演员们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他们在贵族之家受到接待,在许多情形下还应王室之命演出。但教会仍然指责戏院为传播丑闻的学校,并根据此种认定,将所有的演员逐出教会,而且禁止他们死后被葬在教堂墓地——包括巴黎的一处墓地。伏尔泰指出其中的矛盾:
演员由国王付薪酬,却又受到教会的驱逐出教;他们每晚应国王之命演戏,而又受到教会的禁令做任何表演。如果演员不肯表演,他们将受到入狱下监的惩罚;如果他们表演,那么在死之后,又要被贬黜到阴沟里。我们很高兴与演员一同生活,却反对与他们埋葬在一起,我们让他们与我们共餐,却不准他们进入我们的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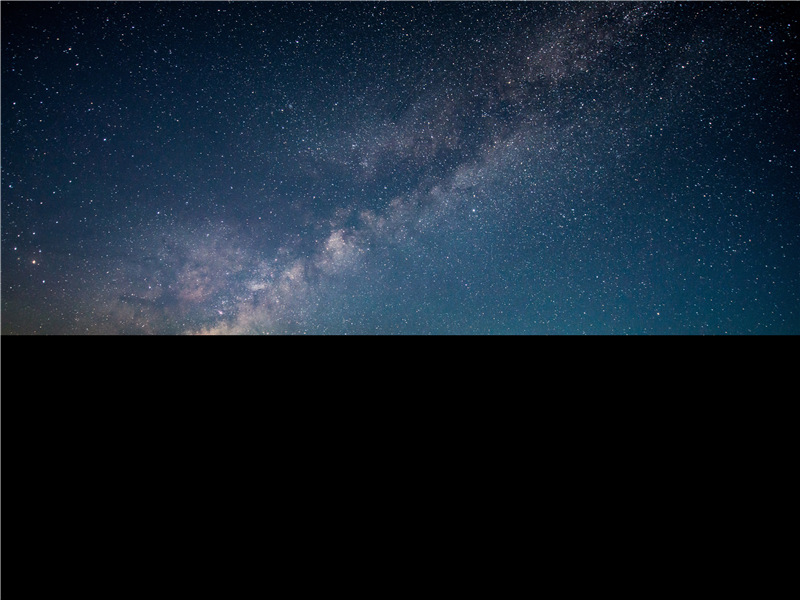
当时最伟大的女演员勒库夫勒,以她的生死阐明了以上的各种正反对比。她1692年出生于兰斯附近,10岁时前往巴黎。由于住在法兰西剧院附近,她时常溜进戏院,待回到家里,则模仿她钦羡的那些悲剧人物的动作。14岁时,她组织了一群业余者,在一些私人舞台上从事表演。演员勒格朗教授她一些课程,并为她在斯特拉斯堡演出的一个剧团里谋得了一个位置。与莫里哀一样,她曾多年在各省扮演各种角色,也毫无疑问地一次又一次地恋爱。她渴望着恋爱,遇到的却是色情狂,有两个人相继使她怀孕,却又拒绝与她结婚。她18岁时生了一个女儿,24岁时又生了一个女儿。1715年,她回到了巴黎,而年轻的伏尔泰就在其时其地遇到她,两人曾有过一段超友谊的关系。1717年,她成为法兰西剧院的首席女演员,实现了她幼年时的梦想。
同许多其他著名的女演员一样,她并不十分漂亮。她可以说是相当结实,而五官也不寻常,但她在姿态举止上有着无法形容的优雅,声音似乎带着诱惑的音乐,她漆黑的眼眸里,更闪烁着火一般的光彩与感情,在她面庞上,更有着跳跃与华贵的表情,她的每个动作都表现着个性。她拒绝遵照法国戏剧表演传统的演说风格。她决心像实际生活那样在舞台上自然演剧、谈吐,唯一例外是字正腔圆,加大音量以让最后边的观众听到。她在短短的一生中完成了戏剧表演的划时代革命。这一革命也建立在她情感的深度、表达热情与爱的温柔的能力,及在悲剧中完全的凄恻之上。
老年人赞美她,年轻人则为她丧魂失魄,形同痴傻。年轻的伯爵费雷罗,即将成为伏尔泰代理人,他对她的狂热使他母亲警惕,怕他可能会向这位名女伶求婚,便发誓要送他到殖民地。勒库夫勒听到这个消息后,写信给费雷罗夫人(1721年3月22日),保证她将使这位年轻男爵的殷勤失望:
我将依照你任何意思写信给他,如果你想如此,我也可以再也不见他,但别威胁着送他到地球的尽头去。他对国家有用,他能够成为朋友的宠儿,也会以满足与美名来为你加冕,你需要做的,只是引导他的才分并让他的美德发挥出来。
她的判断十分正确,费雷罗伯爵后来升任为巴黎议会的一名议员。他85岁时,整理他母亲遗留下来的信件,偶尔发现了这封信,以前,他丝毫不知道有过这回事。
她随后也经历了爱的一切狂喜、沮丧与拒斥。年轻的撒克逊王子莫里斯,常常来观赏她的演出。那时,莫里斯王子虽然尚未战功彪炳,但早以其英俊与浪漫闻名,王子向她表白将对她终生爱顾时,勒库夫勒认为这正是她等待已久的英雄。1721年,她接受他为爱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生活在如此柔情蜜意的相互忠贞中,巴黎人将他们比为拉封丹故事里热恋的斑鸠。但这位已是军队元帅的年轻军人,却梦想着王国。我们已提到他赶往库尔兰寻求王位,并接受勒库夫勒的资助。
勒库夫勒借着成立一个沙龙来安慰自己,这使她得到一种智慧之赐,她学到了拉辛的文雅与莫里哀的观念,她渐渐成为法国最有教养的女人之一。她的朋友并不是那些偶来的慕名者,而是一些喜爱其智慧的男女,丰特内尔、伏尔泰、费雷罗、凯吕斯伯爵经常到她家共进晚餐,不少贵族夫人也高兴地参加那个才气洋溢的团体。
1728年,那位失败的军人回到了巴黎。他现在才认清勒库夫勒较自己年长4岁,为36岁;另有十几位富裕的妇人,都愿与他同床共枕。其中一位几乎与王子一样尊贵,就是布永公爵夫人,她也是波兰贵族英雄让·索别斯基(Jan Sobieski)的孙女。公爵夫人在法兰西剧院的包厢里非常大胆地带着莫里斯在勒库夫勒面前炫耀,勒库夫勒这时正面对着舞台上的包厢,带着加重的语调背诵拉辛《费德尔》一剧中愤怒的语句:
我绝非那些厚颜无耻的妇人,
她们能面露平和地犯着罪行,
在罪恶外表高竖着一道篱笆,
而从不会羞耻地感到脸红。
1729年7月,一个名叫西蒙·布雷的微型画画家和修道院主持,通知勒库夫勒小姐,说有两个戴着面具的宫廷夫人代表曾向他提出,如果他能给这位名女伶服下毒药丸,则他可获得6600利维尔的酬报。勒库夫勒于是通知警察,拘捕了这位修道院主持,严加询问,但这位主持坚持他说的实情,她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给警察局副局长,要求释放这位修道院主持:
我已经与他谈了很久,也使他谈了不少,而他始终是很恰当很机巧地回答着。我并不希望他说的合属实情,我有一百倍的理由希望他可能是发了疯。啊!我只须恳求上帝的赦免。但是,大人啊!如果他是无辜的,请您想想看,我将多关心他的命运,而他命运的不定,对我又将是多么残酷啊!请不要单单考虑到我干的行业与我的出身,务请体谅我的灵魂,在这封信中,您可以看出那是多么的赤诚与坦白。
布永公爵坚持这个修道院主持应该加以拘押。几个月后,这位主持被释放了,但仍然坚持那个故事是事实。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知道那究竟是否属实。
1730年2月,勒库夫勒小姐开始经受着日渐恶化的腹泻,但她仍在戏院演戏。3月初,她在一次昏倒中被人抬离。3月15日,她以最后的一股力气,演出伏尔泰《俄狄浦斯》一剧中加桑特的角色。3月17日,由于肠发炎而非常危险地流血不止,那位元帅王子不再前来,只有伏尔泰、费雷罗伯爵照料着她。3月20日,她死在伏尔泰的怀抱中。1849年,尤金·史克里布与欧内斯特·勒古韦在巴黎制作了他们成功但不十分确实的剧本,剧名就叫《勒库夫勒》。1902年,弗朗切斯科·奇莱亚(Francesco Cilèa)也以同样的主题,写了一出歌剧。
因为她拒绝过教会最后的礼仪,根据教会法,她不得埋葬在教会墓地。她的一个朋友雇了两个拿火炬的人,将她的遗体搬上一辆出租马车上,秘密地埋葬在塞纳河畔,那里现在已成为勃艮第大道。伏尔泰写了(1730年)一首诗,名为《勒库夫勒小姐之死》,激奋地指责这个葬礼的不尊重:
所有的人心皆如我心,
为这桩悲伤已极的事感动。
我从四面八方听到
那些受挫的艺术含泪喊道,
墨尔波墨涅啊!
你再也不存在了!
明日的你将做何话说?
当你知道,
那些没有心肝的人,
在这些被遗弃的艺术上,
横加日趋枯萎的伤害?
她若在希腊当赢得圣坛的荣耀,
在此却不得埋葬!
我曾目睹他们崇拜着她,
环拥着她;
而刚一逝去,即成罪犯!
她吸引这个世界,
你们却惩处着她!
不!
这两旁河岸,
将绝不亵渎;
它们护持着你的灰烬,
而这悲哀的荒丘,
对我们将是座新的神庙,
受着我们歌颂的荣耀,
更因为你的余荫得享圣名。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剧作家,当然非伏尔泰莫属,然而他也有着许多对手,如克雷比永。1705年至1711年,克雷比永曾创作了好些成功的剧本,而后,由于受到《薜西斯》(1714年)与《塞尔拉尔斯》(1717年)两剧决定性的失败,他认为自己才华已尽,从撰写剧本的行业退休,陷入穷困之境。他在他的阁楼里养着10条狗、15只猫与一些乌鸦,聊以自慰。1745年,蓬巴杜夫人以一笔津贴与一份闲差事拯救了克雷比永,并安排由政府印刷厂出版他的作品集。他于是前往凡尔赛向夫人致谢,虽然卧病在榻,她仍躺在床上接见了他。正当他弯身亲吻她玉手致敬时,恰巧路易十五走了进来。这位70多岁的老翁随即叫道:“我完了,国王当场抓着我俩了。”路易十五欣赏着他的急智,也与蓬巴杜夫人一样,怂恿他完成那被放弃的有关喀特林的剧本。该剧于1748年首演时,夫人与其他宫廷贵人都加赞赏,克雷比永再度享受着美名与法郎。1754年,他80岁那一年,他写了最后一个剧本。之后,他又活了8个年头,而乐与他的那些动物为伍。
伏尔泰并不乐见这位从坟墓中现身的竞争者。在喜剧方面,他也得面对着那位多才多艺又兴致勃勃的马里沃的竞争。马里沃是在偶然情况下,变成一位讽刺作家的。有一次,他看到他那年仅17岁的情人在一座镜子前,摆弄着种种诱人的姿态。他的心脏只是短暂地悸动一下,因为他父亲在里永一地负责钱币制造,许多的年轻女郎都想变为马里沃的妻子。他是为了爱情结婚,他过着很节制的性爱生活,使巴黎人因而吃惊。他常出席唐森夫人的沙龙,可能就在夫人的沙龙里,学得了融入他剧作里的轻巧机智、优雅用词与细密情感。
马里沃第一部成功之作是《爱的闹剧》,1720年曾盛况空前地在意大利剧院连续演出12次。正当他啜饮着演出的成功时,约翰·洛的银行突然破产,使他损失了大部分钱财。据说他借着一管笔又赚回了这些钱,他写了一长列的喜剧,以他独特优雅的揶揄与聪明的情节,愉悦着整个巴黎。所有喜剧中最有名的是《爱情与机会的游戏》,剧中叙述两位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妻,他们同时但不一致地决定,去试探对方的忠实,他们主仆——男主、男仆与女主、女仆——在衣着与举止上各自易位,而发展出有如苔丝狄蒙娜的手绢一样荒谬的许多有关的巧合。巴黎的妇女对马里沃喜剧中那些爱的纠缠与温柔感触,要比男人喜爱得多。在这方面,也与凡尔赛宫和沙龙里一样,或与华多和布歇一样,女人君临一切,享有最后的决定权,情感的分析取代了政治问题与战争英雄的谈论。莫里哀以男性为主的喜剧逊位给以女性为主的喜剧,除了博马舍外,这种情形一直延长到斯克里布(Scribe)、小仲马和萨尔杜(Sardou)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