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位文艺女神来自希腊
在古老的历史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妇女过着像希腊女性那样的较自由快乐的日子。古典时代的雅典人信奉多位女神,他们相信专司美丽与欢乐的优美三女神以及分掌文学、艺术、科学等的缪思九女神固然是女性,而守卫正义,智慧与和平的天神也是女性,他们的城邦以主神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命名,还在雅典卫城的最高点上为她立了一个栩栩如生、俯瞰全城的雕像。
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文明达到最高峰,然而她给妇女带来的不一定全是好处。历史文献对雅典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几乎不提一字,但对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上层妇女多有记载,上流社会的贵族生活,要求妇女行为举止必须毫无瑕疵。她们必须使自己免遭丈夫的白眼,否则她们的情况就会非常不妙,一位贤淑妇女几乎要做到足不出户,受过良好教养的女人如果公开露面,就会成为一件丑事,因此除了若干宗教或家庭庆典外,一般不准踏出家门,即使上街购物也在禁止之列。因为可以由丈夫或奴隶代劳。当时有一些绘画和雕塑描述了雅典富裕封闭的阶级妇女,与闺阁中生活的情形。闺阁通常设于楼上,远离街道,供妇女过与外人隔绝的生活。尽管雅典人对天上诸位女神心存敬仰,雅典许多男性公民对待女性的态度。却好像女性的生存,只是为雅典男人传宗接代似的。倒是其他地方的妇女显得更有活力更有灵性。

对于莎孚的个人经历,我们所知极为有限,只知道她也许结过婚,而且生了一个名叫克莱丝的女儿。以当时的眼光看来,莎孚一定不是漂亮出众。她长得又矮又黑,而当时的标准是又高又白才称得上美人儿,莎孚大概为了躲避国内战乱,曾在西西里岛叙拉古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即返回来斯佛斯,显然在那里度过晚年。不过,后世重视的不是莎孚生活上琐事,或性方面的癖好,而是她的诗歌。一般学者都同意,即使她的诗篇留存下来不多,亦足以支持柏拉图后来的见解,认为她是古典世界第十位文艺女神。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帝国渐趋分裂,最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互争雄长。在公元前431年爆发战争。西欧史亡称之为第二次伯罗奔龙撒战争,这场惨烈战争在断断续续打了30年后,文化较落后的斯巴达才把雅典彻底击败。最奇怪的是,败方雅典的妇女,反而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实际得益者,数十年绵长战争的确为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带来不幸,但由此产生的社会变动,使雅典的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正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使整个西方世界的妇女开始获得解放一样。伯罗奔尼撒战争虽未替古代雅典妇女完全解除枷锁,至少也放松了几分束缚。
当时古希腊妇女的婚姻,通常是基于利害关系而撮合的。出于真爱的结合只是极少例外。妇女如被发现与人通奸,会从严处罚,并且贬低身份,但她们的丈夫乱搞男女关系,宿娼或者狎玩,则视作“正常”行为。做妻子的主要职责,只是料理家务和照顾儿女,而且做这些事情亦要避人耳目。如果有什么特别事情她必须涉足别处,那么事后她就要费好一番唇舌向丈夫解释。丈夫宴请男客时,她不能同桌吃饭。她的任务只是将食物准备妥当。然后让丈夫和宾客大喝大嚼,自己则回到闺阁进食。
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缠斗不休,这种情形逐渐有了很大改变,公元前404午,亦即战事实际进行了27年后,雅典终于投降,许多旧规常法亦一去不返。这时,雅典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摒弃了过时的习尚,活一天算一天,尽情享受的态度也已蔚然成风。据说在一次围城之后,城中人口四分之一以上死于瘟疫,大政治家培理克里斯也不能幸免。生还者中,军人兼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记载了这次灾难对公众道德的影响:“人人亲眼看到命运陡变的景象,富人一夜之间死亡,财产给穷人占去了,这一切使人宁愿公然纵情享乐,不必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他们寻求暴利,在这个肉身和财富都时刻可能幻灭的世界,把即刻的自我满足视作合情合理的追求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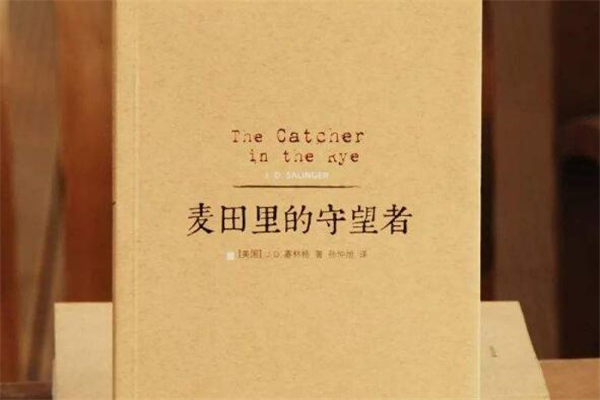
当时的希腊人都抱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想法,而雅典妇女大概也不落男人之后,趁着这一股新起的自由开放风气,做起一些心中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来。这一方面雅典妇女倒是追随死敌斯巴达的榜样。因为斯巴达虽则军纪较雅典严明,然而他们却鼓励妇女多与外界接触,多到四处活动,享受人生。
雅典剧作家幼里披底作品中一个角色解释说:“斯巴达少女可以走出屋外,光着大腿,穿着紧身衣,与年轻男子一起竞跑和角力。”但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不仅是斯巴达少女,连雅典少女也开始扯高裙子,享受野外风光。这股风气引起了不少麻烦,所以到了下一世纪,当局不得不委派一名官吏专责管束雅典城内妇女,他的特别职责是防止妇女挥霍无度。在男人看来,要限制女人花钱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在雅典历史中,妇女终于首次争取到人权,而且妇女越来越明白她们原来拥有不少厉害武器可供妇女解放运动之用,只是未懂利用而已。公元前411年,剧作家阿里斯多芬尼斯发表了一出喜剧。描写希腊各城妇女运用她们最具威力的武器争取和平,举行性罢工,不准她们的丈夫碰身子,直至男人放弃打仗为止。但在此之前数年,这种题材的戏剧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