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柏拉图还是对人类事务感兴趣。他看见社会的美景,也醉心于那个没有堕落、没有贫穷、没有暴虐、没有战争的社会。雅典政治倾轧的痛苦使他颇感震惊,“失和、敌视、仇恨和怀疑永远循环不已”。他也跟贵族名门一样瞧不起富豪的寡头政治,“商人……对那些被他们毁了的人视若无睹,随时冷不防地把他们的刺螫——金钱——刺进他人体内,然后,收回数倍的本钱:这就是他们使得全国满是游手好闲和贫无立锥之地之人的方式”。然后,民主政体出现,因为穷人已征服了对方,杀掉了一些,放逐了一些,其余的则与穷人同享自由与平等。结果赞成民主的这些人也不比那些富豪高明:他们靠人多势众来赈济人民,自己则居高位。他们奉承人民,纵容人民,结果自由变成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一切标准都因无处不在的粗鄙而贬值,风俗也因随便滥用和没遮拦的侮蔑而变粗俗。正如对财富疯狂的追求毁了寡头政治一般,自由的滥用也毁了民主政治。
苏格拉底: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无政府状态,连每一户住家也都受到波及,最后连各种动物都不能幸免……当父亲的已习惯于和儿子处于同一地位……儿子既不敬畏双亲,也无羞耻之心……校长怕学生、阿谀学生,学生轻视校长和教师……老少不分,年轻人与老年人平等,并且随时都可能和老年人为一句话、为一件事争胜。老年人……模仿年轻人。我也不该忘记谈到男女之间的自由平等……真的,连马驴都开始以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姿态昂首阔步……一切都可能随自由毁灭……
阿狄曼图:那么结果呢?……
苏格拉底:物极必反……自由过分,不管对国家或个人而言,都只有变成奴役……最令人讨厌的暴君,也是由于极端自由而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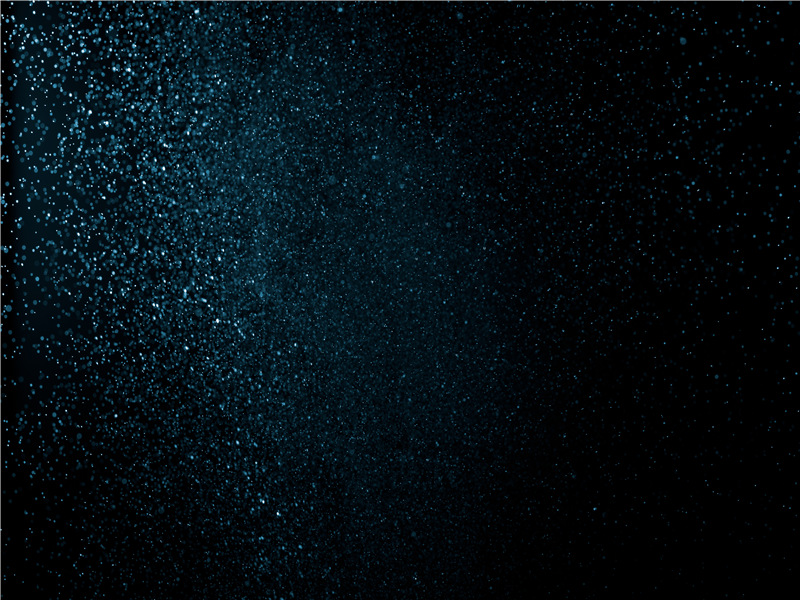
当自由太过放肆时,独裁就会接踵而至。有钱人惧怕民主会榨取他们的钱财,因此协力来推翻它。或者由某个有进取心的人掌权,对穷人许下天大的诺言,然后组织一支私人军队来保护他,先宰了敌人再杀朋友,“直到他整肃了整个邦国为止”,然后建立独裁政治。在这种两个极端势力的冲突中,劝人保持中庸、彼此理解的哲学家的处境有如“被野兽包围的人”。要是他够聪明的话,他就一定“躲在墙角,任由狂风暴雨吹过”。
有些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就以过去自娱,著述历史。柏拉图则以未来自娱,塑造理想国。首先,他认为我们得先找到一位仁君,肯让我们与其子民一起试验。其次,我们得把成年人全部遣走,只留下维持治安及教诲年轻人所需的成人,因为长辈会使这些年轻人重蹈他们的覆辙。所有的青少年,不分性别、阶级,一律先施以20年的教育。课程内容包括神话——不是原有的那套不道德的神话,而是能使这些年轻人变得驯良、孝顺父母、忠于国家的那些神话。 20岁时接受体能、智能和道德三方面的测验。考试不及格者列入理想国里的“经济阶级”——成为商人、工人和农人,这些人可以保有私有财产,并依能力的不同保有不同等级的金钱,但不许有奴隶存在。初试及格者再受10年的教育及训练,到30岁时再接受一次考试。复试不及格者成为军人,这些人不许有私人财产,也不许经商,住在军事管理的共产社区中。复试及格者用5年的时间研究各科“神圣的哲学”(divine philosophy),从数学和逻辑到政治和法律。到35岁,这些人学成之后才让他们回到社会上去谋生、去奋斗。到50岁时,这些还活着的饱学之士不经过选举,自动成为监护或统治阶层的一分子。
这些人有权而无财。理想国里没有法律,一切法律案件和争端都由这些“哲学王”(philosopher-kings)根据智慧来作判决,不受先例影响。为了避免他们滥用权力,这些哲学王不许有恒产,也不许有金钱、家庭或妻子。荷包的事由老百姓来管,刀枪的事由军人来管。这种共产并不民主,而是贵族式的,老百姓无力胜任,只有军人和哲学家才能做到。至于婚姻方面,每一阶层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奉监护人的这种优生誓约的约束:“最优秀的男女应尽可能和最优秀的异性结合,较劣的与较劣的通婚,而且各阶层的父母只能抚养该阶层的子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人种的优异。”小孩子一律由国家教养,享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各阶层的区分并非世代相传的。女孩也有和男孩同等的机会,任何政府机构不得以某人是妇道人家而不录用。柏拉图认为,由于有个人主义、优生学、男女平等的主张以及贵族政体等的结合,将可能产生一个哲学家乐于安居的社会。最后,他又下了一个结论:“除非哲学家可以为王,或是世界上的皇族都有哲学的精神与才华……否则城市必然因充满罪恶而毁灭,整个人类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