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后的反思
据说苏联人在康韦尔完成《冷战谍魂》之后,在希腊与他接触过。为此,在他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时。他明确表示不愿去俄国。但另一原因可能起着支配作用,即情报官员在他们离开特务机关之后的五年内,不准去铁幕国家的条例。康韦尔相信,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仍有必要进行。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特务机关在这场斗争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觉得斯迈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熟悉,因为“对读者或观众来讲,阴谋本身是一种安慰剂。人们想用阴谋两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阴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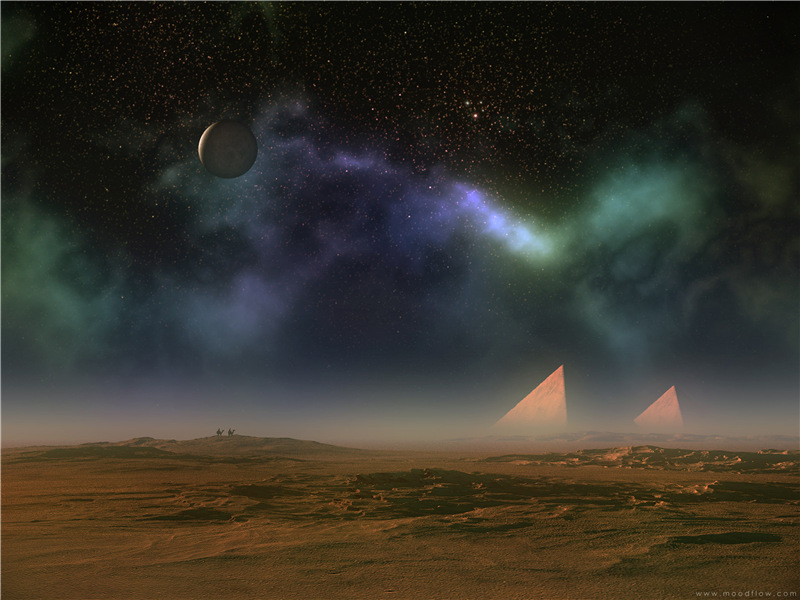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合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子,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这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25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

